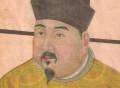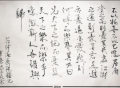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撰稿:三喵先生
策划:三喵先生
责编:马戏团长
全文约4000字 阅读约10分钟
所谓“以史为鉴”,这件事情顶重要的前提是以诚实之心面对过往的一切,而不是加上很多扭曲的滤镜。可惜的是,很多情况下后人面对的历史的确已经是不那么诚实的记述了,在这种情况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算是一个很自然的结局。
我个人觉得,“靖康之耻”是一件很足以塑造当代中国人性格的大事。这件事情的影响不仅是一些诗词作品和武侠小说的设定这么简单,在我看来,它把传统文化中所谓的“道学”推广到了非常高的地步。
自20世纪以降,出于许多宣传的目的,靖康之耻又被反复拿出来重提了好多遍,那么古代的华夷之辨在近世的话语体系中就会以各种新的方式被重新述说(比如那句又被捡起来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 这种看起来很有精神的口号,还被某现象级电影直接拿来用做宣传
但无论如何,许多这样豪气干云的话语背后,都隐约藏着对靖康之耻的恐惧。
那么很自然地,靖康之耻这件事情究竟缘何而起,当真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了。
但可惜无论是过去还是近世,对这件事情的起因大抵都是从道德角度切入且浅尝辄止,即使如金庸先生,也只好说出这样的话来——
“想当年徽宗道君皇帝一心只想长生不老,要做神仙,所用的奸臣,像蔡京、王黼,是专帮皇帝搜括的无耻之徒;像童贯、梁师成,是只会吹牛拍马的太监;像高俅、李邦彦,是陪皇帝嫖院玩耍的浪子。道君皇帝正事诸般不理,整日里若不是求仙学道, 便是派人到处去找寻希奇古怪的花木石头。一旦金兵打到眼前来,他束手无策,头一缩,便将皇位传给了儿钦宗。那时忠臣李纲守住了京城汴梁,各路大将率兵勤王,金兵攻打不进,只得退兵,不料想钦宗听信了奸臣的话,竟将李纲罢免了,又不用威名素著、能征惯战的宿将,却信用一个自称能请天神天将、会得呼风唤雨的骗子郭京,叫他请天将守城。天将不肯来,这京城又如何不破?终于徽宗、钦宗都给金兵掳了去。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
当然作为小说家而言,金庸先生这么写是毫无问题,但很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许多话被许多人当了真,然后以此作为信史铭记在心了。
我自己对于“以史为鉴”是持有非常悲观的态度,所谓“以史为鉴”,这件事情顶重要的前提是以诚实之心面对过往的一切,而不是加上很多扭曲的滤镜。可惜的是,很多情况下后人面对的历史的确已经是不那么诚实的记述了,在这种情况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算是一个很自然的结局。

◇ 《汴京之围》书影
这本《汴京之围》我之所以推荐给大家,盖因此书很诚实地记录了靖康之耻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而且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很克制,没有借着手头的历史材料洋洋洒洒地过多发挥自己的见解。
一个合格的历史研究者应该在对材料的叙述中隐去,而让观众通过自己选取的材料和这些材料呈现的方式让观众明白自己的用心。这该是历史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在当代的许多历史著作(特别是中国古代史著作中),达到这样要求的书委实不多,幸运的是这本书做到了。
如同许多分析北宋末年的著作一样,这本书叙述的历史事件不晚于王安石变法,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造成靖康之耻的因素有很多,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
在这些必然的因素里,北宋作为中国古代帝国的一个典型案例,会有许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冗官冗兵,皇帝要极力防止手下造反,等等等等,而中国古代帝国的几千年历史,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些结构性问题害的一个个朝代以各种方式死掉而已,北宋岂可以幸免?
再说说那些偶然性因素。其实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靖康之耻的直接诱因不是”北宋积贫积弱“,而是非要趁着辽国国势颓废之时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为此不惜撕毁百年盟约,而后来在同女真结盟的时候又反复地出尔反尔罢了。

◇ 燕云十六州
为什么一定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呢?在皇帝来讲是好大喜功,在主战的臣子那里,这是大大的政绩。至于“任何决策的实施该做的基本利弊衡量”,比如收复燕云十六州能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这在当时是没什么人分析的。
不惟如此,传统社会中的许多决策,至少从我接触的史料来看,考虑到一个最基本“成本收益核算”的委实不算太多,很多情况下做决策的依据也只是一时的冲动,然后用一句漂亮的口号或者“一盘大棋”之类的阴谋论给盖过去了。
当然,我觉得庙堂之上作决策的人大约其实是不傻的,之所以做事的后果是如此难堪,大约是有着颇多的难言之隐,比如说,集权官僚体系中,“有政绩”和“不丢面子”是压倒一切的,才不管这个政绩是可能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收复燕云十六州”就是这个的注脚,而宋朝令人无语的地方在于,同样的故事在南宋末年又几乎原封不动地重演了一遍。再后来,类似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传统,大明和大清也很自觉且变本加厉地继承了下来,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 艺术家千万别做皇帝 图为宋·赵佶《瑞鹤图》
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就是徽宗朝那会儿君臣们的心态和德性了。我自己丝毫不掩饰对宋徽宗艺术成就的欣赏,但很不幸,由于他自己亡国之君的结局,他“好声色犬马,舞文弄墨”之类的东西,都被说成是“私德有亏”。
如我所言,很多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往往流于简单的道德判断,而在我看来更不幸的是,许多这样的道德判断其实都没有抓住一些根本性的事情,那么有些皇帝和领导者在传统史学家看来私德很不错,比如明末的崇祯皇帝,他的确和宋徽宗很不一样,非常勤政,但最终大明还是亡了。这至少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传统史学所秉持的道德观是有问题的。
在我看来,所谓勤政懒政,所谓写字画画,其实对于领导者而言都是不那么重要的德行。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德行只有一个,那就是“谨慎和负责”吧。用罗马人的话说是这么几个词,gravitas,责任感;pietas,为家族和国家的奉献精神;还有iustia,对自然秩序下的等级制天然的认同和维护。
从这个意义上讲,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的确是“德不配位”。本来收复燕云十六州和一系列的谋划是庙堂之上君臣的主意,而北宋的军力不强,这样收复燕京的“宏业”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赵良嗣的外交努力得到的。
日后由于徽宗皇帝的一系列操作让金国人找到了撕毁合约的借口出兵北宋,宋朝君臣选择让赵良嗣背锅把他杀了。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明末崇祯皇帝的作为里。
在这里,这几位领导人不管是否勤政,在这个根本性的德行上是有着严重的缺失。站在这个最根本道德的角度来讲,所谓的“德行匹配”是一个真理。一个人总归要德行匹配的,要么是真的具备某个位置上应有的品格而受人尊敬,要么就一定会因为基本的道德缺失而遭遇严厉的惩罚,换句话说,德行总要匹配,in one way or another。
再说说这个iustia,那就是关于“自然秩序”和一些相关的推论。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弱肉强食的纯粹丛林世界,大约是因为人类不太会把弱者赶尽杀绝,而这种维护弱者权益的东西,大约就是“契约”之类的存在了。

◇ 大卫·劳合·乔治(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第一代德威弗尔的劳合-乔治伯爵。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在1916年至1922年间领导战时内阁,在1926年至1931年间担任自由党党魁
1914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议会谴责德国并呼吁对德宣战,他认为德国践踏了契约精神,而这种契约精神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正是凭借这几张微不足道的支票和汇票,几张小小的纸就可以驱动万吨巨轮在大西洋两岸穿梭运输。这种基于互信的契约非常珍贵......”诚然,我周围有相当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坚定地认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嗯,在很有限的几个极端案例中,这么做可以理解,但倘若一个人把这样的鸡贼龌龊当作人生观贯穿人生,或者一个国家把这样的不守信用当作基本国策来指导国家大事,等待他们的除了悲剧就毫无其他,这正是历史的教训。
我一向不认为“落后就一定会挨打”,倘若如此,世界上那么多相对落后的团体和国家大约就不要活了。在我看来,从历史中得到的教义是这样的,“不守契约大概率会挨打,已经落后了还理直气壮地不守契约,就一定一定会挨打”。在这个层面上,靖康之耻才是有启迪后人的意义。
所以徽宗的悲剧不是什么声色犬马,而是“轻佻”二字,所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当年宰相章淳的话还是蛮准的。
可惜的是,靖康之耻之后没多久,大家就把这些很容易从史料中得到的东西忘掉了,大约选择遗忘是逃避痛苦的方式吧,可是痛苦就在那里,并不是通过逃避就可以看不到的,所以如《汴京之围》书里所言,中国古代的许多男人把亡国的苦果推给了女人。
南宋的时候关于妇女节烈一事特别看重,这和靖康之耻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在后世的道学家们看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中国的男人们大抵都是可以成为圣贤的,只不过女人红颜祸水罢了”。
类似的事情,在明末和清朝又发生过好多遍,太阳底下无新事嘛,古今中外皆然——1944年盟军解放法国之后,在德国人铁蹄下唯唯诺诺了四年的法国男人义愤填膺地揪住了许多“同德国军官睡觉”的法国姑娘,把她们剃了光头游街···多么熟悉的画面。






◇ 法国沦陷期间,他们对德国人唯唯诺诺,法国解放了,他们重拳出击,把“不洁”的女人的头发剃光了,这一刻,在这些光头女人的旁边,他们挺起了腰杆儿。得意洋洋的表情在说:嘿,朋友,今天我又惩治了几个纳粹
当然,许多这样认真的思考大抵是很不讨喜的,所以面对沉重的历史,激昂的口号或者文艺的缅怀都是蛮不错的止痛剂吧,作为前者,自有许多打鸡血的言辞在;而作为后者呢,我常常会想到徽宗皇帝那首“北行见杏花”的词,那是他被押往金国北地之时写的东西。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无做。”
想到这些,会对他有颇多的同情在。但作为半个开封人,有时候我会拿起北宋时期开封都城的图来看,看那些“曹门”,“繁塔”,“金明池”之类熟悉的地名,再想到这些地方在我小时候的样子,那点对徽宗皇帝的同情也就会消散许多。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配图源于网络,若有侵权,后台联系删除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