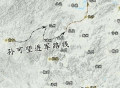刘刚/文
南明遗音
孟德斯鸠咨询中国文化,除了那些商人,还有一位中国人。
那人名叫黄加略,福建莆田人,生于天主教家庭,七岁丧父,母亲将他托付给传教士李斐理,李斐理请当地儒师教他中文,自己教他天主教神学和拉丁文。后来,李斐理又把黄加略托付给主教梁宏仁,1702年,梁宏仁往罗马汇报礼仪之争,带黄加略同往。从厦门乘英轮出发,次年,到达罗马。三年后,他们在巴黎候船,要返回中国,但因梁体有恙,而滞留下来,黄亦因此不能回国,遂定居巴黎。
当时,巴黎流行中国风,经人推荐,黄加略留在法国教中文。此后,又受聘为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官,1711年,因其翻译成就,被冠以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称号,两年后,娶了一位法国妻子,过着清贫的日子。
因为清贫,妻子常常抑郁,有时整日不语,乃至绝食,但他却处之泰然,依然头戴礼帽,腰佩剑,往来于知识界的各种社交圈,出入于主流社会的各阶层。应该说,他赶上了好时候,在那些“中国风”吹拂的日子里,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骄子,法国人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样式,看得又感动又好奇。
有人这样说道:这个中国年轻人,令我感动,他比那些禁欲主义者们更加沉得住气,虽然身处异国,生活拮据,且无以生财,靠一笔不定的津贴,维持其生计,却有一份雅致,令人惊奇。还说:这一切都使我相信先前人们对“中国人”的描述。“中国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原来都是听说的,现在便有这么一位,而且就在跟前,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样本,可供观瞻。但当时所有人几乎都忽略了一点,他们在黄加略身上看到的,已不全然是中国文化的样子,而毋宁说是中西合璧式。他本来是作为基督教在中国培养的一个成果,被传教士梁宏仁带到欧洲来展示的,他的气质与仪表,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式,但不是那种“耶稣+孔子”。
有关礼仪之争,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梁宏仁带他来,是用传教的实际成果,作为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相结合的一个例子,来回答有关礼仪之争的问题。
但他似乎并未引起教会和教皇的注意,可谓辜负了梁的一番苦心孤诣,然而,他在法国,却如同一件美丽的中国瓷,被人珍惜,其风姿仿佛梅瓶,亭亭玉立,不但一下子就引起路易十四的注意,把他留下当了中文翻译,而且引起了知识界的兴趣。
有一个问题从未有人问起,他在法国,戴礼帽,穿礼服,如何处理从清朝带来的那根辫子?跟他接触过的人,都没提到辫子,有可能他被剪掉了辫子。若果如此,那就该问一问,是在出国前,经由基督教洗礼后就剪了辫子,还是出国以后,为了展示传教成果的需要才剪了辫子?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清初之时,福建沿海一带,是反清复明的前线,继南明政权后,郑成功又建立了台湾政权,清政府又是海禁,又是迁海,折腾得东南玉碎,半壁难安,故其地山野之民,多未蓄辫。凡此种种,不管由于何种情形,总之他没有辫子,可能这是他难以回国的直接原因。
那时,一个没有留辫子的中国人,多是别有怀抱的伤心之人!
我们不好说他本人或其父黄保罗就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但东南半壁的国风民调,沿海一带的人心民意,常怀故国之思,多蓄烈士之志,而为革命契机。
清初之时,复明志士多以出家,做和尚,做道士,逃避迫害,这样做了,最起码可以不留辫子,若出家做个天主教的教徒,是不是也可以不留辫子呢?岂止不留辫子,甚至可以做得更多,以至于国朝蒙难之日,君臣纷纷受洗。据说,易代之际,南明小朝廷为能续命,而救亡图存,竟然向罗马教皇求救。
这可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了,它能安抚亡灵,却救不了亡明。
更何况教皇远在天边,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教皇对满清、南明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留有一手,汤若望等留在北京,投靠满清。也有传教士,与之相对,进入大西政权,南明小朝廷中,天主教官员更多,几乎完全将南明朝廷天主教化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瞿纱微,南明永历帝时,两宫太后、皇后乃至于太子都由其亲自洗礼。
一名西方传教士,竟然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的反清复明运动,而且至死不回头,他那光明的内心里,有着怎样颠扑不破的信念呀!对于那个南明小朝廷来説,上帝太高了,教皇太远了,血雨腥风中,只有他不离不弃,永远的陪伴在永历帝的身边。
当永历帝被广州的官吏背弃时,太监庞天寿亦有去意,来问他,他说:天主教徒处大事时,不可计生死,应崇天主而忠于君。广东官吏之拥戴永历为帝,公为主谋,由是而应患难相随,助其复国。与其走,勿宁死,使后人知君为忠臣,以身殉主。
经此一劝,庞天寿便留下来,抱定了同永历帝共生死的决心。
中国历史上,不乏忠义之士,然而,在宗教信仰的加持下,迸发出忠义,这还是第一次,中国人的内心里,除了杀身成仁的信条,灵魂不灭的意义也觉醒了。历史呀,请记上这一笔!别忘了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神的国度,曾经有过那么一些天主的信徒,他们在王朝中国的世界里走上绝路,最终走向信仰救赎。
永历帝灰心丧气,瞿纱微为之诵读《圣经》之《申命记》和《罗马人书》,前者系摩西诫命以色列人,让耶和华神为其选立国王;后者则有耶稣对信徒宣称,世上任何权柄皆系神命。他说:我们天主教徒不畏生死,其中一项美德,便是效忠皇帝。
救兵来了,就近的救兵,从澳门来,三百葡萄牙战士,带着枪炮,跟着瞿纱微来了,枪炮齐鸣,清军退走,永历帝得救。在为两宫太后洗礼后,他又预言收复国土,果有两广之地归附,故其声望倍增,以此,加速了南明小朝廷的天主教化程度。然而,怎奈清兵一而再,再而三,继续南下,径取粤、桂,不得已,永历帝奔黔,为护帝,瞿纱微以小舟潜运,自乘大船,吸引清军,故缓行,于桂、黔交界处被追至,不幸遇难。
读南明史,我们发现,像瞿纱微这样的传教士,不止一个,还有许多。于是,难免要问一声:他们从南明小朝廷究竟看到了什么?何以如此为之失魂落魄?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牵挂着总也放不下,结果连性命都搭上了?
那是为了他们的国呀!是为了他们与南明合作的一个政权,那是以“孔耶同源”作为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神圣合一、神王合一的国度,在欧洲已经失去的——政教分离,他们正在从中国找回来,福音险中求,天国在人间,孔子受难,耶稣受难,他们也在受难,苦难与辉煌,如金声玉振,似交辉相映,那是上帝留给文化中国的一曲悲歌。
永历四年秋,帝制衣带诏,秘授波兰人卜弥格,其中有致葡萄牙国王书,致威尼斯共和国诸公,上罗马教皇英森诺书,致欧洲耶稣总会长帕科罗米尼书信。
1651年,卜弥格等人自澳门乘船出发,用了两年时间,到达欧洲,欲求救兵,然而,却被各国冷眼相看,原因是,与其同时到达的传教士卫匡国,正周游列国,宣告满清即将征服中国,还说这在中国,已然大势所趋,欧洲无法改变,惟有顺应。
可怜卜弥格,受尽冷眼后,带来的信都递出去了,眼看没有回应,借兵无望,而时光流逝,就想回转中国,回到永历帝身边去。当别人都在逃离时,他回来了,回到了澳门,却遭到驱逐,不得不转由东南亚入境中国,就这样,卜弥格身心俱疲,一头栽倒在广西边境,他再也起不来,离中土就差那一步了,却终未能见永历帝最后一面。
卜弥格死后,不久,永历帝也被吴三桂所擒,被绞死于云南。
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南明小朝廷,就此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它似浪花一朵,可卜弥格就为了看它最后一眼,才不远万里,冒死而归,因为从他眼中所见,那可是天国在东方的投影,被天主的光辉沐浴过并启示着,他与此浪花呀,有着灵魂的契合。
一个中国人在巴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加略的父亲受洗了,教名“保罗”,人称“黄保罗”,赶上了“反清复明”的那个时代,即便未能投入其中,然一方水土所系,难免风化。那时代,有两个最强音,一个是“反清复明”,还有一个便是“哈利路亚”,它们都是南明历史遗产,虽由耶稣会士领唱,但耶稣会却因明清易代而分裂:一投南明,一靠北清。
卜弥格和卫匡国的欧洲之行及其游说教廷,就将中国的南北朝分裂,带到耶稣会内部来了,也分作南派、北派,并且在欧洲公开化了。南明亡后,南派随之消失,但那两个时代的最强音,却是他们留下来的,北派在康熙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北派延续着耶稣会的上层路线,而南派遗留的传教空间,则被主张“到民间去”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填充了,黄保罗、黄加略父子所在的教会,就是外方会,在南明留下的历史遗产里传教,在“哈利路亚”的赞美声中,永远挥之不去的,便是“反清复明”,在接下来的“礼仪之争”中,对祭天、祭祖、祭孔的否定,就暗含了“反清复明”。
因此,在“礼仪之争”中,捍卫中国礼仪的神性,就是捍卫大清,而否定中国礼仪,也就否认了大清。教会“反清复明”,用的是南明永历政权作为标准,同样是中国文化,为什么信仰的差距那样大?南明能接受天主教洗礼,为什么北清不能?
外方会以此否定了中国礼仪,首先,它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拜孔子是偶像崇拜,祭祖是迷信行为;其次,它指出,耶酥会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旨在迎合中国统治者的喜好,经不起朝代更替和政策变化的考验,造成了在华传教的不确定性。故其力促教廷禁止中国礼仪,主张尽快落实教会本土化,采取走下层群众路线的传教策略。
梁宏仁从中国返回欧洲,带回来的大概就是这些观点,黄加略受其影响,对中国礼仪的看法,同他差不多,如果说梁用他的看法对教廷和教皇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黄加略则用自己作为一个中国文化边缘人的看法,对孟德斯鸠产生了影响。
哪一个的影响更大呢?梁宏仁影响了教皇,教皇否定了中国礼仪,这就影响了东西方,清朝拒绝了教廷的一神要求,耶稣会从此退场。而外方会,因其进入文化边缘地带和政治异议空间,活动虽隐蔽,范围却越来越广,传教程度亦更加深入。
黄加略对孟德斯鸠的影响,可说的要更多一些,这主要是因为许明龙的著作《黄嘉略与法国早期汉学》,对黄加略在欧洲的言行,做了尽可能多的搜集和整理,其中有一篇,就是孟德斯鸠撰写的《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
当时的欧洲,不光中国哲学成为显学,而且中国文化也成为了流行的“中国风”,中国问题,是关乎欧洲未来、回答“欧洲向何处去”的一个关键问题。
面对中国问题,历来都是采取主流文化立场,以解读中国哲学的方式来认识,这已经成为欧洲知识界的共识,而孟德斯鸠则反之,他有着天生的民粹情怀,有着自觉的文化边缘取向,据说他出生后,按照法国的习俗,要给他找个教父,而家里给他找的,却是个乞丐,名叫夏尔,这就时不时地在提醒他:孩儿呀,穷人是你的教父。
如此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确立了他作为思想者的民间立场,作为知识人的边缘化倾向,所以,他面对中国问题,就不是一头钻进中国哲学里去请教朱熹,请教孔夫子,就像伏尔泰与莱布尼茨,而是去请教那些从中国回来的商人,请教像黄加略那样在中国没有任何功名、缺乏主流文化背景的知识边缘人,故其看法难免有失学衡。
黄加略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知之者不多,在礼仪之争中,也轮不到他发言,尽管他在《罗马日记》里,对祭祖、祭孔都有看法,但那也是自言自语,并未对外宣讲,而当时法国知识界也是把他放在主流文化上来看的,看作是主流文化的样子。他要在法国安身立命,就得维持这个样子,而不能将其内心和盘托出,否则那些与中国有关的项目,如《汉语语法》、《汉法字典》就不会让他来做了。
他刚开始做时,对于语法一窍不通,让他来做,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似乎理所当然,就应该成为法国上流社会期待的香饽饽。他在法国的优势,就因为他是“中国热”里唯一的中国人。当时就有人说: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是一件人人关注的事。而他就是那个被关注的中国人。
路易十四时代,为中国人准备好了一个最美好的时刻,上流社会的门,向中国人随时开着,一个“中国孤儿”,一名中国穷小子,居然在巴黎登堂入室。
历史上,只有那一刻,为中国人准备着,享受过那一刻的,也就他一个,一个中国人的路易十四时代,说起来很美好,看上去也不错,但日子并不好过。
难道他就不想回国?我们来看他在巴黎的日记里说了些什么。他很想回国,因为日子难过:
这日子没法过了,国王的中文翻译,听着好听,钱少事多,连图书馆工作人员都给我脸色,书都不帮我搬;上个月,赊账做了身文官服,服装店的人今天上门了,没钱付。明天让妻子去比尼昂馆长的办公室要年金。然后,他长叹一声:算了,算了,谁让我回不了中国呢!
曾有过一次回国的机会: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两个职员来找我,问我能不能随船去中国两年,给他们做翻译,当掌柜。听起来能发财的样子啊!心动!可心动归心动,心动还得转变为行动,但行动却停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计划搁置了,回不了中国了。可惜啊!巴黎最近肉太贵了,只啃得起干面包了。
他本来早就可以回国的,梁宏仁原本也是那样安排的,但礼仪之争问题,被教皇敕令解决后,康熙帝恼怒,下令驱逐传教士,他若回国岂不要撞枪口了?所以,他选择了留在法国,不回中国,而且没去教会任职,直接为国王工作,他这次未能成行,有可能是没有得到路易十四的允准,他毕竟是一位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说走就走。
不能回国,就得另谋财路,他发现:耶稣会的神父写的什么玩意,画的牛鬼蛇神都说是中国的特产动物,这样的书都能一版再版。反正耶稣会不是外方会,骂两句没关系,骂着,骂着,他突然开窍了:那我来翻译本好书,不就可以赚大钱?
他从国王图书馆里找了本《玉娇梨》,认为那些才子佳人故事,很符合法国人的品味。可他才翻译了一半,就有人对他说,这样的作品在法国没有市场。感谢上帝!刚好这时,比尼昂馆长给他发了年金,还另有一笔额外津贴,他就收手了。
当然,他也有快乐的时候,快乐中的快乐,是一见相知。他说:最近,有位年轻的孟德斯鸠先生经常来拜访,说他对中国的事情很好奇,问了许多问题,尤其是中国政治。那时,孟德斯鸠“漂”在巴黎,无学业,无职业,共计“漂”了54天,其名字,七次出现在日记里,平均下来,将近每周一次。有一天,孟德斯鸠对他说,要把我们的谈话,写成一本关于中国的小册子。没过多久,这本小册子就出来了,他说:我看到孟德斯鸠先生写的那本小册子了,我姓Hoang(黄),不是Ouanges(王),罢了,罢了,法国人也发不出来H这个音。
那本小册子,就是《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后来,孟德斯鸠出版《论法的精神》,共有31章,其中,论及中国的就占了21章53节,可见中国问题,在这部巨著中的分量,其论据,一多半,就来自他与黄加略的交谈。
谈话内容,涉及到了中国的宗教、刑法、服饰、墓葬、家产观念、文学、科举、妇女地位、国家性质,他向这个年轻人完全敞开了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那些言论,会对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发生影响,因而不朽。
他那副敞开心扉的样子,也被孟德斯鸠写在了《波斯人信札》的前言里,作者说:书中写的那些波斯人,曾跟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处。他们把我视为另一个世界的人,对我什么都不隐瞒。亚洲人了解法国风俗更容易,因为我们喜欢敞开心扉。
有人说,黄加略就是《波斯人信札》里的“波斯人”的原型。
在与孟德斯鸠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讲了自己作为中国人在巴黎被人围观的情景。七年后,那情景在《波斯人信札》的第30封信里,如实呈现出来:初到巴黎时,我被视为天外来客,男女老少无不以目睹为快。我一出门,所有人都趴在窗上看我。我到杜伊勒里宫,四周立刻围上一圈人。如此殊荣不免成为一个负担,我不认为自己如此稀奇。于是,我脱下波斯服,穿上了西装。不同在于,他被披上波斯服,外加两撇小胡子。
据说,黄加略当年购买西装的账单,至今还保存在巴黎档案馆。
知遇伟人,他分享了伟人的不朽,碰到小人,他难免要皱眉头。在日记里,还有小人:傅尔蒙先生最近来得倒是殷勤,怎么感觉傅尔蒙先生在偷偷抄我整理好的中法词典资料呢?傅尔蒙先生那个兔崽子居然在外面公开讲演我的研究成果,不想教傅尔蒙先生中文了,他在外面说我法语差,我哪里法语差了!我七岁在家乡莆田就跟着法国传教士学法语,在法国也生活十几年了!居然说我法语差!气死我也!比尼昂馆长让我继续把翻译的进展汇报给傅尔蒙先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这位傅尔蒙先生看来是他命里的修昔底德陷阱:居然明目张胆来我家搬资料,我还没死呢!
对于另外一位合作者弗雷莱,他倒诚恳地怀有几分歉意:弗雷莱先生被抓到巴士底狱了,据说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演讲得罪了当局;弗雷莱先生家人来找我要中文书籍了,他在狱中,还想着学中文,法国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这么宽松吗?我不敢去看弗雷莱先生,怕惹祸;弗雷莱先生从巴士底狱回家了,脸色十分红润,人也胖了不少,据说他家人每日往监狱里送冷切鸡;弗雷莱先生最近对我有点冷淡,是不是怪我没去监狱看他?
后来,这两位都成为了著名的汉学家,然而,对于教他们中文的黄加略却只字不提,他们关心的只是他留下的成果,为此,两人还打起了官司,如此情形,令人想起存在主义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而幸运的是,他与孟德斯鸠相知,不但作为“波斯人”的原型出现在《波斯人信札》里,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也帮助孟德斯鸠回答了中国问题,在《论法的精神》里,向着欧洲流行的“中国热”,泼了一盆醒脑的冷水。
让世界冷静下来,让欧洲回归理性,路易十四时代终结了,欧洲开始向着君主立宪转型,而中国,却还有一笔历史的老账要算,那就是结算反清复明。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